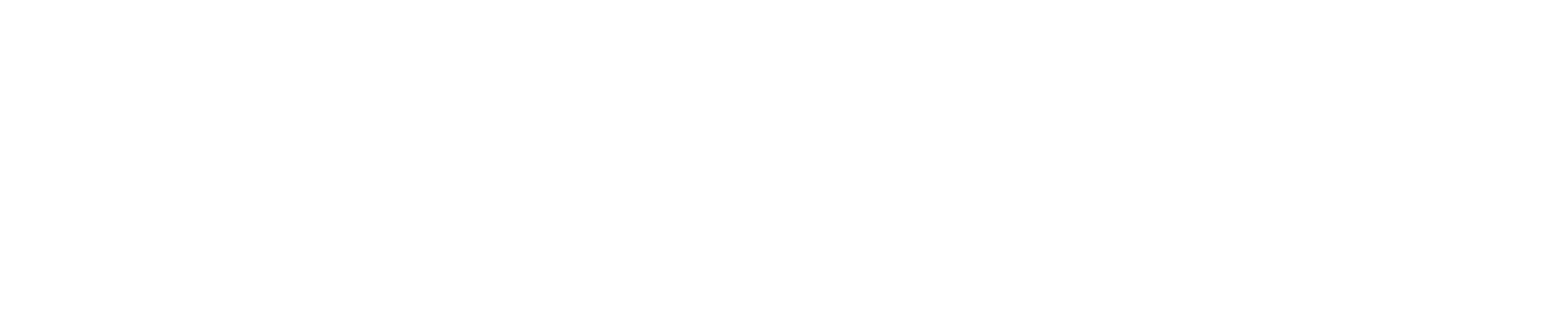实证纪法|如何根据《条例》对政治攀附等非组织活动进行认定处理
我们党历来强调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。党章规定党员要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,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要求,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、培植个人势力、结成利益集团。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在第五十四条新增“政治攀附”内容,将其作为明确概念引入党纪规范,释放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严肃查处“七个有之”问题的鲜明态度。
在党内搞团团伙伙、结党营私、拉帮结派、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是为了小集团在政治上的私利,相互提携、互通款曲,一般有相对固定成员,侧重于评价团体中的核心、主要成员;“政治攀附”则一般用于评价下级或次要成员,指其通过依附、攀附特定的上级个人或团体,通过非组织手段谋取自身政治利益。结合实践,政治攀附行为一般有三个典型特征:一是人身依附性。行为人抛弃政治品格,将个人前途寄托于“靠山”而非组织,将个人进步归因于特定对象的“恩情”而非组织信任,混淆了上级和组织的关系,从而在较长的时间内与特定对象形成相对固定的关系,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封建“主仆”关系。二是利益交换性。行为人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想方设法进行利益输送,甚至主动向特定对象(包括特定对象的特定关系人)寻求利益交换、权权交易,以求融入“圈子”、变成“自己人”,从而谋求“政治前途”、结成“利益同盟”。三是组织破坏性。行为人的攀附行为严重影响了良好政治生态的涵养形成,干扰了党内选人用人机制的正常运转,滋生了私情取代公心、关系取代原则的风腐温床,使严肃的党内生活变成了捞取个人利益的“私人俱乐部”,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常见的攀附手段有物质型攀附,即行为人通过赠送财物、安排消费,或以权谋私、损公肥私使特定上级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进行“示好”;服务型攀附,即行为人搞无原则服从,通过提供各类私人化、定制化服务,想方设法为上级提供便利,以增进“私人感情”;信息型攀附,即行为人通过泄露个人掌握的各类信息,以示“亲近”、拉近关系。
对于政治攀附的认定,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。
一是明确政治纪律属性。从执纪监督中可以看出,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搞政治攀附,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投机钻营、搞旁门左道,本质上是缺乏政治定力和政治自律。政治攀附的政治纪律属性,一方面体现在行为人所攀附的领导干部往往身居重要岗位、重点部门或有重要影响力,其攀附行为超过正常的人际交往限度,滑向团团伙伙、结党营私方向,已经不能简单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廉洁纪律或违反工作纪律等来评价,存在必须查处的政治危害。另一方面,搞政治攀附行为一般具有谋取人事利益、跑官要官等特征,但行为人所谋求的不是短期内简单的职务调动或提拔,其搞人身依附和贴靠的意图是形成较为紧密的利益团体或政治团伙,以期在较长时间内有“后台”、可以搭“天线”,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,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,具备违反政治纪律的属性。
二是注意构成要件变化与情节把握。“政治攀附”行为发生在《条例》修订之前的,若证据显示程度较轻、恶性不大,虽具备一定非组织活动的特征,但尚未达到与“团团伙伙、结党营私、拉帮结派”等程度相当的情况下,一般适用政治规矩条款;若证据显示政治攀附程度深、恶性大,虽然达不到“三人成伙”的人员规模,但已经与其他典型的非组织活动程度相当,则可以适用搞非组织活动的相关条款予以认定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在写入“政治攀附”时没有要求“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”,即无论行为人是否因攀附行为获得实际利益、产生恶劣政治影响,只要存在政治攀附行为,即涉嫌违反本条规定。此外,本条规定的加重情节是“导致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的,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”,在实践中要注意收集反映党组织建设、党风廉政情况、干部队伍建设、群众满意程度等方面证据,慎重判断对区域政治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,避免认定虚化、泛化、简单化。
三是核实行为人的攀附故意和攀附行为。政治攀附评价的是位于从属地位的、意图向上攀附的行为人,表现是行为人更为主动,双方互动性不强。证据链构成要聚焦行为人的主观故意,围绕其明知自己实施的是攀附行为、谋取的是不正当政治利益进行取证,同时注意调取体现客观攀附行为的证据,以达到主客观相一致,避免单纯主观归责、客观归责。实践中,认定搞政治攀附是否需要证明被攀附对象知情存在一定争议。我们认为,虽然政治攀附的单向性较为明显,但攀附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被攀附的领导干部谋求利益,即便是通过领导干部的特定关系人进行攀附,最终也需传导到领导干部处才具备实现可能,因此被攀附的领导干部至少应当概括知情。此外,还要注意区分正常履职行为和政治攀附的界限,结合行为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,辨析是否超出正常工作范畴。